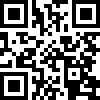古代诗人确实有才,鲜花也确实有形有色有生命。服饰是人的创造物,难怪文思敏捷的诗人,一观花入迷,便在花中看到了服饰。
如梨花,可以使人产生若驾春风,拟步青云,仿佛进入天上仙境的错觉。唐代殷尧藩曾写:“云满衣裳月满身,轻盈归步过流尘”句,而且梨花在春风吹拂下的姿态,还可以令作者想到洛神的轻盈、神秘和美妙绝伦。
玉兰花开九瓣,色白微碧,香味似兰,仅从形象上看,就容易使人联想到白璧无瑕的玉女。明代文征明写道:“绰约新妆玉有辉,素娥千队雪成围。我知姑射真仙子,天遣霓裳试羽衣……”看来,那一簇簇盛开的晶莹似雪的玉兰花,真的使作者陶醉了,他恍惚看到月中嫦娥率领仙子婆娑起舞。王灼《碧鸡漫志》中说:“开元六年,上皇与申天师中秋夜同游月中,见一大官府……素娥十余人舞笑于广庭大树下。”这其实是一种文化奇观,并非自然景观,因而明初四家(画家)之一的文征明才会想象到这种诗情画意。紧接着,作者想到,这些容貌娇美的白衣仙子,不是正在表演那“此曲只应天上有”的霓裳羽衣舞吗?与文征明同列明初四家的沈周,也是在玉兰花摇曳的姿态中,看到了一系列的服饰之美──“翠条多力引风长,点破银花玉雪香。韵友自知人意好,隔帘轻解白霓裳。”
牡丹可谓国色天香,由于唐代时人们崇尚牡丹,而牡丹那造型饱满、色彩浓艳的特点,又恰如盛唐的绝代佳人杨玉环,因而围绕着牡丹的诗词很多,诗人也极易在牡丹花上看到动人的服饰形象。唐代李商隐就写过一首:“锦帏初卷卫夫人,绣被犹堆越鄂君。垂手乱翻雕玉佩,折腰争舞郁金裙……”卫夫人是春秋时期卫灵公的夫人南子,南子就是个有名的美妇人,犹如盛开的牡丹;鄂君是楚王的弟弟,传说他以绣被堆在越女身上,好似含苞待放的牡丹;至于玉佩、郁金裙等更是形容牡丹花开经风吹动时宛如舞动着的一群美女……
李白曾写:“一枝红艳露凝香,云雨巫山枉断肠。借问汉宫谁得似,可怜飞燕倚新妆。”这里说即使体轻如燕,能在宫人所托水晶盘上跳舞的赵飞燕天生丽质,还要倚仗新妆,而国色天香的牡丹和花容月貌的杨贵妃却是完全自然的美。实际上这里都有个服饰形象的联想。宋代范成大写牡丹品种之一“叠罗红”时,就因其花瓣重重叠叠,从而想起女子百褶裙的褶皱──“襞积剪裁千叠,深藏爱惜孤芳。若要韶华展尽,东风细细商量。”范成大另一首写牡丹名品之一“崇宁红”时,写道:“匀染十分艳艳,当年欲占春风。晓起妆光沁粉,晚来醉面潮红。”
明代王衡写牡丹名品之一“二色红”时说:“宫云朵朵映朝霞,百宝栏前斗丽华。卯酒未消红玉面,薄施檀粉伴梅花。洛阳女儿红颜饶,血色罗裙宝抹腰。借得霓裳半庭月,居然管领百花朝。”这里“红玉”一词,古人多用来指美人肤色。《西京杂记》中载:“赵飞燕与女弟昭仪,皆色如红玉,为当时第一。”诗人由牡丹花的风姿颜色想到美人的醉态晕妆,甚至想象为美人为了减却红晕,故意薄薄施上一层檀粉,以与梅花相伴。“血色罗裙宝抹腰”,更是由花及人又及衣,血色的罗裙是诗人由红牡丹的颜色想到的,“二色红”牡丹中的深红者因有黄蕊,被人称为“间金红”。花瓣上有一道金黄色的粉线,分外妖娆。
古人曾写“微带紫而类金系腰”,这都因为服饰形象给人的印象太深了。宋代彭元逊曾写一词《平韵满江红》,也是从牡丹想到服饰形象,虽说这首咏牡丹词述说的是失意文人在困难深重时代的心绪,但依然引用女性服饰形象来发出感慨──“翠袖余寒,早添得、铢衣几重。何须怪、妍华都谢,更为谁容……山雾湿,倚熏笼……”无论诗人看到的是一枝从吴宫流落到人间的牡丹花,还是失宠后流落到百姓家的宫女,都是通过服饰的变化去显示出这一社会现象的。
明代杨基《咏七姊妹花》中“红罗斗结同心小,七蕊参差弄春晓。尽是东风儿女魂,蛾眉一样青螺扫”,“红罗”(裙)、“同心”(结)、“蛾眉”“青螺”说的是面妆和化妆材料。宋代黄庭坚写“酴醾花”:“汉宫娇额半涂黄,入骨浓薰贾女香。日色渐迟风力细,倚栏偷舞白霓裳。”也是通过“涂黄”(面妆)和“薰香”以及“白霓裳”来表现花儿所显示出的佳人形象,使诗人不禁咏物感伤。当然,有的虽然也从花中看到了服饰,可是非常轻松、风趣、俏皮的词句给人以美好的感觉。如宋代杨万里咏“金沙花”:“双松树子碧团栾,红锦缠头白锦冠。尽放花枝过墙去,不妨分与路人看。”写院中的两棵松树相依相偎,像是一对情人在倾诉衷肠。满树新生的松子圆圆的且又青翠,好似玲珑的佩玉。酴醾花与金沙花飞上松树头,洁白和红艳的花朵竞相齐放,似乎是舞人头上缠着的巾帕和锦冠,好一番舞人的美服盛景。